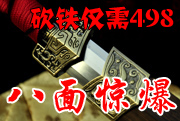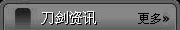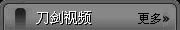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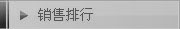


历史上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考
历史上,中、日、朝三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领域十分宽广。在这部经常为三国人民引为美谈的史册中,我们注意到,在兵器与武艺的交流方面,也写下许多精彩篇章,其中尤以剑刀武艺的交流内容丰富,引人入胜。一般说来,中、日、朝的古代刀剑武艺,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历史,民族风格上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但是,由于长时间的相互影响,交叉渗透,使三国在武艺领域里产生了许多共生现象,不少具有共同特点的东西一直遗存到现代。显然,这些共同点正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以剑刀技艺为主体的所谓“短兵”体系,从来都是中国古代武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日、朝武艺交流的重心所在。这个问题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牵涉到许多尚待探索的史事,而我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待今后的努力,特别有待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总之,历史上三国之间的武艺交流活动,直到今天还在以体育文化的形式延续着,并且显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这一点着眼,研究这个问题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就自不待言了。首先对古代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活动进行研究的,是已故学者唐豪先生。(1)步唐先生之后尘,1980年,我发表过一篇研究中日剑刀武艺交流的文章,曾被译介到日本,多少产生了一些反响。(2)忽忽二十年过去了,出于对此问题的特殊兴趣和责任感,我不断搜求新的材料,认识也有所跟进,早就萌生旧作重写的念头。在这篇新作中,我将把一些新材料和新认识补写进去;同时,为了扩大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又将中、朝武艺交流的若干史事也纳入其中。然而,既限于个人水平,又限于所用资料毕竟以中国文献居多,论述恐仍旧不免于偏隘。
先父马凤图(健翊)生前对保存中国的日本双手刀法非常珍惜,不但要我郑重保存因流传不广而幸未遭到流俗浸染的刀法,而且一定要下功夫去研究它的渊源,认真清理明代以来我国出现的多家双手刀图谱,使这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显扬当世,传存后代。我1980年那篇旧作,就是遵从先父的嘱咐起笔的,然而初稿完成时先父已溘然作古,正式发表竟一直拖到“**”恶梦醒来以后……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再度撰写这篇文章时,的确深深感觉我的研究进度太过滞缓,至今为止,仍然还有很多问题说不大清楚,还有不少工作需要继续做下去。思之,真是愧对先父遗教,不免为之汗颜等级:11人球童一
我国的武艺起源极早。它的内容和形式总是因时变易 ,时代不同,特点各异。同时,在武艺形成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曾产生了军旅武艺与民间武艺的分野,还贯彻着技击因素与健身因素依存消长的矛盾。总而言之,武艺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它的发展史同样也是相当复杂的。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古代,在冷兵器在战争中据于主要位置的历史条件下,武艺的社会价值首先决定于它在战争中和各类社会冲突中的防身杀敌之效。因此,它的内容就不能不以临阵实用的兵器技术为主体;它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同兵器形式的发展变化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由此推之,任何武艺形式的传播与交流,也必然以兵器的传播交流为先导,为载体。
一般认为,早在周、秦时代,我国制作的剑刀等兵器就已传入日本,其传入途径主要是朝鲜半岛。日本的古文献和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日本与古代韩国之间存在一条所谓“海北道中”的交通路线,历年来,在日本北九州发现了大量的先秦铜剑和铸剑的铜范。在北九州发现的很多“是锋刃锐利,具备完整特色的中国产品”。(3)而相同的兵器在韩国原属弁韩、辰韩的庆尚南北道也多发现。多年前,日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先生曾经指出:“这些事实说明,中国文化产品的铜剑、铜铎,远在二千几百年前的古代,就经过弁韩、辰韩、对马等地,先传到博多湾沿岸,然后传到筑后、丰后方面。因此可以推断,这条线是当时的主要交通线,恰好同《书纪》中所说的海北道中一致。”(4)另据汪向荣先生说,日本列岛弥生时代,其青铜文化分成两个文化圈,一是铜铎文化圈;一是铜利文化圈。所谓铜利文化圈,就是指北九州地区发现的大量“铜利器”,其中主要是铜剑等兵器。在佐贺县的瓮棺土葬的原始古坟地带和怡土郡的支石墓中,都发现了为当时统治者用于陪葬的铜剑等兵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这些随葬品中,除了极少数可以认为是当地仿制者外,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上来的舶载品。”在铜利器传入同时,制作技术也随之传入,这为铸型(熔范)的发现所证明。(5)在朝鲜半岛的许多地方,都挖掘到中国先秦时期的铜剑,进一步证明在中、日、韩三国人民的早期交往中,剑已成为传递文化和联络感情的媒介物之一了。(6)到了汉代,中国制作的各类短兵器,尤其是铁制环首大刀,曾大量流入日本,对日本短兵器形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环首大刀兴起于西汉初期,它是在剑,特别长剑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一种新式短兵器。由于汉代铁制环首大刀刀形轻便,锻造精良,战阵实用之效很高,因此特别受到日本武士的喜爱。1962年,在日本奈良天理市栎本古坟的古墓中,发现了一柄东汉中平年间(184-189)中国制作的铁制环首刀,刀身镌有“百炼清刚,上应星宿,下辟不祥”等金错铭文。(7)这柄刀的形制、铭文格式及刀的质地,与1974年出土于我国山东苍山的东汉永初六年(112)铁制环首刀基本相同。它们都是用反复加热、多层叠打、表面渗碳的工艺制作的优质含钢铁刀。(8)中平刀作为殉葬品出土于日本古墓,证明墓主生前喜爱之深,也成为汉刀传入日本的可靠物证。据《日本武器概说》的作者未久雅雄说,日本各地曾有不少汉刀和日本对汉刀的仿制品出土。他认为,当时日本武士所用的兵器,“特别是通过朝鲜半岛从大陆移入的”(9)。汉刀的大量流入日本,对日本刀制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从日本古代兵器史著作中所看到的日本古刀,许多都具有明显的汉刀特征。据《中国兵器史稿》的作者周纬先生说,汉刀的仿制品在日本随处可见,“常有收藏至数十器者”。
可以肯定,古代中国的剑刀,主要是通过民间途径进入日本的,但也通过两国间的正式交往进入日本。最著名的例证就是三国时日本邪马台国同曹魏之间的交往。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载,日本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曾于魏明帝曹睿景初二年(238)六月,派大夫难升米等来中国通好。魏明帝盛情接待这些友好使者,并回赠了一批珍贵礼物,其中包括“五尺刀二口”。其后,两国互通使者,多次来往,在魏国每一次馈赠日本的礼物中,也总是有刀。 证明到三国时代,中国制作的刀仍然受到日本人民的珍视。日本九州熊本县玉名郡兰水町江田船山古墓中,曾发现刻有汉字铭文的日本大刀,日本学者认为这是五世纪中期的遗物,约当中国的南北朝时代。(10)这柄刀的发现,证明中国剑刀对日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三国以后。日本考古学家小野胜年先生曾说,著名的日本正仓院里,至今还保存着不少古代中国的剑刀;“献物帐”上还记有“唐式大刀”、“唐刀”等名目。(11)所谓“唐式大刀”应指唐代军中盛行一时的陌刀,这种刀的样式在中国已无实物可证,只有日本正仓院还保存有几柄唐代实物。(12)这些都证明历史上中国剑刀对日本的影响是久远的,至少延至唐代,中国剑刀仍在继续传入日本。
早在秦、汉时代,就有大量中国人经由朝鲜半岛移居日本,他们融合成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很多贡献。据日本古文献《雄略纪》、《书纪》等的记载,汉代的大陆移民往往以其手工技艺被分为“部民”,如手人部、衣缝部、鞍部、画部、锦部、陶部等,这些“部民” 给日本带去各种手工技艺,受到日本朝野的重视。没有关于金属锻铸工匠移居日本的记载,但有诸如弓削、矢作等兵器制作者,可以肯定,中国的剑刀锻造工艺必定也传入日本。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中国兵连祸结,加上各族政权凭借武力互相吞并掠夺,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迫使不少中国人涉海移居日本,这些移民同样也是按其技艺分为部民。这时期,因为传统的朝鲜半岛路线被阻断,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主要转向南朝,于是南朝文化对日本产生很大影响。自春秋战国以来,我国南方,特别是吴越地区,以精美的剑刀锻铸工艺闻名天下,同时楚地的长剑武艺独步海内,历久不衰,直至汉代还是“奇材剑客”的渊薮。相信这些都可能随着日本与南朝关系的持续发展而传入日本。(13)隋唐两代的遣隋使和遣唐使,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那时,日本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的成员,除了各级官员以外,还有各种专业人员,其中总有占总数近半的“射手”,实际就是使团的护卫武士;还有“锻生”和“铸生”。这些人员的配备,主要是为了预防船舶漂流遇险,但他们入唐以后必定在本专业上学到很多东西,并将其带回日本。(14) 我们注意到,入唐的日本官员和留学生也有对兵法武器感兴趣者,如著名的遣唐副使吉备真备就是一位大唐兵法兵器的爱好者,然而他每次带回日本的中国兵器中,只有马步漆角弓、平射箭、射甲箭等各式弓箭,却没有剑刀。(15)这是否说明此时日本自产的剑刀已相当精良,再无须从唐朝引进。
日本人民是以善于吸取外来文化而著称的优秀民族。长期借鉴中国的经验,结合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使日本的剑刀锻铸工艺获得突飞猛进,并终于超迈中国而后来居上。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花纹剑,特别是兴起于春秋末期、发达于两汉的钢铁花纹剑刀,曾以其无与伦比的锐利精致而冠绝世界。考古发掘所得,往往在深埋于地下千百年后,依然锋刃如新,绚丽夺目,使中外人士叹为奇观!然而,由于遭受历代统治阶级的漠视、摧残,这种先进工艺到唐宋以后竟渐至衰退。与此同时,日本的花纹剑刀却异军突起,大放异彩,“数百年来,在远东首屈一指”。(16)大致自宋代开始,日本剑刀开始向中国输入,随着时代的推移,输入量愈来愈大,对中国剑刀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据《宋史·日本传》记载,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曾经入宋求法的日本名僧奝然为报答宋朝对他的礼遇,谴弟子喜因奉表来谢。在喜因赠献宋室的方物中,就有日本制作的“铁刀”。实际上,宋代日本剑刀已通过民间贸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在中国享有“宝刀”之誉。请看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写的《日本刀歌》: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让妖凶。诗人说,中国古代传说中能够“切玉如割泥”昆吾之剑,早已渺茫难求了,(17)而在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却造成了真正名不虚传的宝刀。从诗人的咏赞中我们可以想见,日本刀不仅锻造精良,而且装饰也极考究,所以“好事”者不惜重价购求,竞相佩带以炫耀利器。“百金”并非虚语。据日本《宇治拾遗物语》中说:“以太刀十腰(把)为质,则可自唐人(指宋代中国人)借来六七千匹之物。”(18)足见当时的日本刀确实价值昂贵。正由于此,日本剑刀终于成为日本对中国贸易的只要出口品之一,这不仅在宋朝是如此,在元朝也是如此。(19)到了明代,日本刀的制作臻于极精,传播日远,声誉日隆。从文献记载和保存到今天的实物来看,明代的日本刀一般刀身修长,刃薄如纸,锐利无比,挥动起来十分称手,确有穿坚断韧之效。从刀形上观察,不难看出日本刀继承和发扬了汉代环首大刀的优点,尺度和分量都更加有利于格杀技术的发挥。与唐宋以来形制驳杂、刀体厚重的中国短兵器相比较,日本刀无论外观上和实用价值上,都确实要高明得多。 明代日本剑刀大量进入中国,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
第一,是日本王室和商家对明廷的进献,对此类进献,明朝一般都有超值“回赐”,本质上是朝贡贸易。明初,明太祖鉴于倭寇侵扰和胡惟庸里通日本的罪行,对日本进献的方物一概拒不接受,并实行海禁政策。据日本古籍《善邻国宝记》记载,日本为了恢复日中贸易,于明建文帝三年(1401)派使者奉表通好,并“献方物”,其中就包括“剑十腰,刀一柄”。明朝的诏书中还特别提到过这柄“宝刀”。紧接着,永乐元年(1403)日本第二次“献方物”时,刀的数量就增加到了一百把。以后所献方物中刀几乎成了最重要的物品之一,刀的品种也增加了。以有记录可查的宣德九年(1434)为例,一次就“献”了撒金鞘太刀二把、黑漆鞘太刀壹百把、长刀一百柄,总计二百零二把。保存下来的景泰十年和成化十九年的两份记录上,所献刀的数量与宣德九年相同,说明二百零二把是定额。(20)由于文献记载缺失,我们已无法得知以朝贡名义进入中国的日本刀究竟有多少。有人做过统计,仅日本足利王室各朝进献给明朝英宗以前各帝的刀,有一千二百余把,这些优质的日本兵器,主要供明廷的“御林军”执用,其遗存至今犹可见到。(21)当然实际数量肯定远远大于一千二百把。
第二,勘合贸易。明初,日本商人往往假借“朝贡”名义,携带私物以进行贸易。所带“私物”中尤以剑刀居多。对此,明朝政府曾一再加以禁限,要求每次“入贡”携带剑刀“毋过三千把”。(22)永乐元年,日本贡使携带兵器在民间卖买,礼部尚书李至刚要求禁止,并没收入官。而初登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对“向慕中国”的外夷表示“朝廷宽大之意”,主张由官方以市价收购。(23)但是,为了对中日贸易有所控制,也为了区分倭寇船和贸易船,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与日本正式签定了贸易条约,规定以后凡日本商船来华,必须携带明朝所颁发的“勘合”,以进行朝贡名义下的贸易。规定十年一贡,人员二百,船只二艘。显然,这个限额远远不能满足两国贸易的实际需要,特别是日方。宣德初,明朝稍有调整,增加到人员三百,船三艘,但仍坚持十年一贡。实际上人船限额很难严格执行,勘合贸易的规模、频率都大于明朝定额。日本商船循例向明朝“贡献方物”,所献刀剑就是上面所讲的二百零二把。此外就是“国王附搭品”和使臣和随船僧俗人等的“自进物”,实际都是商品。明朝不允许民间私鬻兵器,日本剑刀一般统由官方收购,给价很优,“一把刀在日本售价八百文以至一千文,而明朝给价为五千文,可见当时利润竟达四五倍。”(24)后来进口数量骤增,质量也明显下降,价格便跟着落下来,但仍然有利可图。所以日船所带国王“附搭品”和“自进物”中,一直以剑刀为主项,输入量也持续上升。据木宫泰彦所提供的统计数,第一、二次勘合船所带剑刀还不过三千把,第三次就飚升到九千九百六十把,第四次三万把,第五次七千余把,第六次竟达到三万七千余把!第七、第八次各为七千把,第十次是二万四千一百五十二把。这只是所谓“国王附搭品”的数量,其中并不包括使臣“自进物”的数字。如加上“自进物”,仅十一次勘合船输入明朝的剑刀,就应该不少于二十万把。(25)第三,走私。剑刀的丰厚利润不但剌激了勘合贸易,而且必然会剌激走私活动。整个明代,中日之间除了官方所控制的勘合贸易外,沿海一直存在大规模的走私贸易,这是无庸置论的事实。明代禁兵之律甚严,但民间私藏兵器者不少。特别是日本剑刀,以其质量精美,“中国人多鬻之”,(26)成了人们喜好的收藏品,这从明人的诗文题咏中可以窥见。可以相信剑刀同样也会成为走私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日本宽永十一年(1634,明崇祯七年)五月以后,严禁输出兵器。(27)然而,走私活动恐难禁绝。明末清初的广东,市面上就有“红毛鬼子”叫卖日本刀者,因为有澳门这个特殊的商埠,日本刀在澳门随处可见,当然可以从澳门进入内地。(28)总之,从走私渠道进入中国的日本剑刀必不在少,只是我们无从考知其数量罢了。
在明代,国家兵器制作机构还仿制日本剑刀,这早在太祖*武年间就开始了。据清修《续文献通考》卷131《兵器》载,*武十三年(******0)设置“军器局”,所制作的各类刀中就有“倭滚刀”。明武宗正德年间,佞臣江彬用事,曾命“兵仗局”制作“倭腰刀万二千把,长柄倭滚刀二千把。”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正烈,经过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的积极推行,日本式的长刀、腰刀成为中国军队的主要装备之一,后来又被引进到北方边防军队中。这样大量的使用,当然不可能全靠从日本进口,得主要靠自己制造。所以,兵器史家周纬曾说,在中国兵器史上,明代短兵以使用和仿造日本刀为一代特点,这个结论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宋代以后,日本剑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至明代达到鼎盛。明代,与日本剑刀大量输入的同时,倭寇的侵扰给沿海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于是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日本的热潮,日本剑刀也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参与这一话题的有文学家,还有军事家、民间武艺家和科学家。一种国外物品在中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牵涉面如此之广,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从北宋欧阳修《日本刀歌》发端创始,“日本刀”成了一个诗家特定的吟咏题材,这一现象传到明清两代,一直绵延不断。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明代政治家、文学家唐顺之,他曾得到一把日本刀,挥笔写成一首《日本刀歌》。其中咏道: 有客赠我日本刀,鱼须作靶青绿绠, 重重碧海浮渡来,身上龙文杂藻行。 怅然提刀起四顾,白日高高天炯炯! 毛发凛冽生鸡皮,坐失炎蒸日方永。 闻到倭夷初铸成,几岁埋藏掷深井, 日陶月炼火气尽,一片凝冰斗清冷。(30) 唐顺之是明代学人中出类拔萃的博学家,他精通武艺,也参加过抗倭战争,他的《日本刀歌》不仅为这一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内容和特色,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明代日本刀的珍贵资料。当时上乘日本刀的刀身都呈现各异光花纹,这正是汉以前中国优质剑刀的特点,古代相剑家们的本领之一,就是根据这些纹
本商城顾客个人信息将不会被泄露给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
地址:浙江省龙泉市回归工程 | 电话:400-000-6782 13735919193 | 工作时间:8:00~22:00 节假日不休